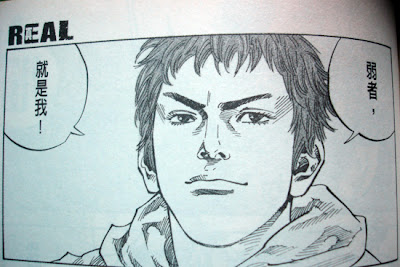Robert capa <<失焦>>
如果你對攝影有一點興趣,你需要知道這個名字:Robert Capa。 羅伯卡帕的名言就是:「如果你拍的不夠好,是因為你靠的不夠近。」這是一句容易被誤解的話,到底甚麼是近?距離上的近嗎?還是心靈上的貼近? 卡帕身為戰地攝影記者,出入世界著名的幾場戰爭(西班牙內戰、第二次世界大戰、越戰),砲火越猛烈的地方,肯定就有卡帕的蹤跡。往後的人們提到他在攝影上的成就,不得不提「諾曼第」登陸的幾張照片。這批照片註定了卡帕名傳千古,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區最重要的一日:「D day」!決定了日後戰事的發展,盟軍成功地逐漸收復被軸心國所佔領的土地。在諾曼第登陸進行之前,卡帕有幾個跟隨的部隊的選擇,最後卡帕選擇了與他感情最好的一隻部隊,一隻登陸的先遣部隊,也就是說卡帕有機會拍到全世界第一張諾曼地登陸的照片,卻也有著同樣高的機率命喪灘頭。過往卡帕有幾次貪圖掌握第一時間的報導並未跟隨部隊深入敵陣,而祇是在交通工具上隔岸觀火,縱使拍到了些人們想要得知的立即消息,未能與弟兄們共進的失落卻讓卡帕難以忘懷。也許如此所以卡帕選了最危險的一隻部隊,在士兵搶灘之際,他也藉由掩體的保護拍下了驚心動魄的一刻。「近」在諾曼地登陸裡得到了卡帕本人的詮釋。不過卻也告訴了我們一件事:黑白底片還是要自己處理比較好。甘冒危險拍得照片的卡帕萬萬也想不到,這四卷底片被《生活》雜誌的傢伙搞砸了,暗房助理戰戰兢兢沖完底片後將烘乾的溫度設定的過高,高到感光乳劑受到破壞,祇有八格底片免強可以沖洗出來。更讓卡帕錯愕的是,刊登出來的報導裡,在照片下方加上了一行字:卡帕的手抖的厲害!不知道是出於渲染報導的張力還是規避責任,總之這句話讓卡帕很不是滋味。 我們今日無緣見識到沒有被高溫搞壞的諾曼地登陸的照片,祇能從茍存下的八格底片一窺卡帕當日的英勇以及戰火的殘酷、猛烈。縱使這八張照片不完美,卻永遠地跟著羅勃卡帕這四個字!不是海明威,不是褒蔓。而是諾曼地登陸。這也讓我們思考戰地攝影師的處境,他們的存在就是將戰場上的各種面向呈現在世界之前,血腥、殘酷、荒淫、暴虐、哀鴻、斷肢、死亡、越來越多的死亡,偶爾加上一點點生活必要的甜蜜。如果你不能拍到這些元素,縱使你有完美的構圖或是精湛的底片處理技巧,也都是無用的。世界祇是要知道他們所無法親臨的現場,究竟發生甚麼樣恐怖的事情?他們祇是要「知道」。更殘酷的事實是,這些今天冒著危險所拍下來的照片,到了明天、到了下個禮...